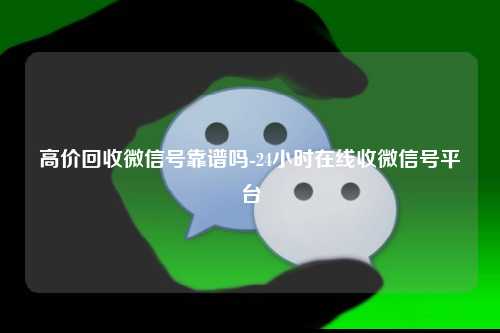朱卫军
此时,我行走在属于自己的故园,沐浴着浓浓的乡愁。人像一只风筝,抑或如一只鸟,无论你飞得多高多远,总有一缕乡情牵着,那根,却是深扎在心灵深处的土壤中,那怕你拽拽一枝一叶,心都是要疼的。
村庄笼罩在忽明忽暗的雾霾中,这是下午三点多钟的时光,太阳依旧灰蒙蒙的,吝啬地献出一点少有的亮色。潮气夹着微风拂面,鼻息里侵入一丝丝废旧塑料和粪便混合的气息,这也许是属于故园的特质吧:所谓的工业园,是废旧塑料回收加工集散地,也许比起当年各自为战的家庭式小作坊,它提升了运营档次,亦减缩了污染;村子周围的庄稼、菜园路边,仍不时地冒出一个个坟茔般的粪堆。村庄已变得面目全非,我承认它融合了许多时代特征和现代意识,人们的生活已非昔日,这有鳞次栉比的一排排新瓦房甚至二三层小楼为证,新农村的容貌已初露端倪。但面对这种变化,心里却又笼罩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我不知道是喜是悲,是祝福还是伤感。那些童年记忆里的美好,几乎消失的无踪无影。
就说眼前的这片阔大工业园,一排排的厂房尽管简易,但却渐成了气候,隆隆的机器声从高高的围墙里窜出来,向着灰蒙的天空飞去。这里,曾是记忆中村里最广阔、最丰沃的土地,大概有数百亩吧,土质黑黝黝的,一攥,甚至都能流出水来,称得上旱涝保收的良田,那时候是被村人称为“聚宝盆”的。我的那篇被《散文选刊》选载的文章《夜潮地》,描述的就是这里的故事。但现在,这片曾经丰盈的沃土上却长出了让许多人欣喜若狂、引以为豪的工业园。也许它给村民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但在我的心里,它却失去了内在固有的灵魂。
我曾用犁耙和双脚深翻过湿漉漉的厚土
把种子与梦想播种在那里
麦子稻子玉米花生,那些被称为庄稼的物种
在我的呵护中闪烁着成长的快乐
最终在粮囤里储蓄着我无忧的日子
它走了,决绝地没给我打一声招呼
也许它给人们的包囊填满了丰盈
可我分明看到被强奸的土地
不住的颤栗不住地哭泣
生于斯长于斯,故园赋予了我的生命我的纯真,亦给我童年青年带来了无限的快乐时光。我沿着村边行走,我试图捡拾那些记忆里汪塘与河流中的童趣。记忆中的村子周边,是有六个充满灵气的汪塘的,泱泱的水面少则几十亩,多则上百亩。那时候,偌大的汪塘清水悠悠,鱼翔浅底。夏日里,片片郁郁青青的芦苇在徐风中摇曳,成群的鹅鸭红掌拨清波。冬天,汪塘冰封,芦花绽放。汪塘里有放养的鱼,鱼儿在水面上不时地快乐跳跃。那是我们这些孩子们的乐园,一进入夏天,放学后窜到那里,把简单的裤衩背心一甩,一个猛子扎进水里,顿觉一股舒适清新亲遍全身。当然也有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比如村东的那个汪塘,水深足有六七米,即使连年大旱,也从没干涸过,传说塘里有深深的渊子,常常会淹死人。但这并没有影响我们在水中的戏玩。但现在,我走遍了村里曾有的几个汪塘,除了仅有的一个已经缩成小小的臭水塘,其余的已全部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新建的亮铮铮的瓦房,里面也许正在氤氲着幸福。我怅然若失。村里还曾有两条小河,清澈的河水里,鱼儿在游动。假日里,我会到河里截上一段,泼干水,定会收获一二斤鱼的。母亲一边埋怨着我又浪费了她的一些油,一边仍在乐此不疲地炒鱼。卷上煎饼,那真是一个香啊。但现在,小河几乎断流,仅存的一点水里,飘着废旧的塑料与腐烂的杂草。好在听说有关部门要投资清理改造这条小河,对我的心伤是一个小小的抚慰。
如果能够穿越,我愿回到记忆里的童年
如同皈依母亲的子宫,桃花园里
红肥绿瘦着我们的爱恋
汪塘、河流里拾取童趣
夜晚的嬉闹笑声,说书人
二胡和踏板的组合声中,破哑的嗓音
演绎着那些久远隋唐五代
记忆已变得遥远
童趣已被岁月的尘埃埋葬
我只能在梦里去寻觅
那些曾经的美丽
我在村里的大街上闲逛,街道宽阔了许多,路面早已硬化,明晃晃的。前几年,村支书也是我的发小,电话里笑着告诉我,村里现在正在搞村村通,从省道到村里的路及主要街道要重修硬化。村里所有的人都要集资捐款,在外工作的,也需要支持一下村里的新农村建设吧,多少不限,当然也不强求。我说责无旁贷,应该的,应该的。为此专门回了趟老家,把我的一点心意献上。等再次回村的时候,看到村路和街道修得真是没法说,它彻底改变了村容村貌,不再是过去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水流淌。我对发小说,你们给村里办了件大好事,是该树碑立传的。他笑着说,你可到村口看看,真是树了碑呢,碑上还有你的大名。至于立传嘛,那就是你这个大作家的事了,有机会你可以写写咱们的村史。我笑笑不语,但就村史讲,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但现在我发现,村里街上寂静了许多,除了老人妇女儿童,行人稀疏。我知道那些年轻些的男女,都出去打工去了。是啊,他们闲不起,在另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里,他们创业挣钱,虽如生长在城市里的庄稼,忍受着艰辛甚至轻视的眼神和怒骂,但他们别无选择。他们走了,留给村庄的,却是漫漫的沉寂长夜。
一季一季的庄稼,呼吸着
阳光雨水和女人的气息生长
汗与泪,打湿了她相思的凝望
那个人,此时会在回望她吗
病床上的婆婆不住的哀怨,嗔骂着对儿子的疼爱
揉着她粗糙的手,抚摸着歉意
她说娘啊,说啥呢,他还不是为了这个家啊
婆媳搂抱着,温暖着彼此的爱意
孩子老师一遍又一遍的电话
留给她些许的怨气
夜晚,星月睡熟了的时候
孤寂袭来,干燥了许久的唇
自己抿了抿,只把思念
一同裹进被窝,温暖那颗
清冷的心
年临近了,该是他的归期
那天晚上我没有回城,住在了堂弟家里——他不让我走,说好久没见了,好好拉拉家常。恭敬不如从命,就住下吧。其实自家房子是有的,那是在坍塌的老屋宅基地上新建的一所房子。这所房子原没有计划建的,因为没人回去居住,但同族的叔叔和姑姑说,还是把老屋翻盖一下吧,等你们父亲百年之后,总得用用吧。想想也是,于是兄弟四个每人拿出一些钱,让堂叔全权代理给操办,建了三间普通的平房。房子是空的,没有任何生活用具生活用品。那晚,叔伯兄弟几个还有发小喝得胡天海地,晕了,真是晕了。散席后我说要到自家房子看看。小小的院落里,弟弟栽植了四棵花树,此时茂盛正艳,也许是寓意为我们兄弟四人的生活吧。靠近南墙,是一小片竹子,“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么,弟弟在栽植竹子的时候,引用了板桥先生的这句话。我们兄弟们在这里诞生,在这里成长,所有的喜怒哀乐,都在这里演绎过。
童年栽种在那里,根深扎于厚墙
我的童趣与老屋的年轮纠缠在一起
直到,它最终推开了我的童年
我仍依旧把它视为
最美的爹娘
多年后,我收视了城市的楼群
蜗居于宽敞几净,遥寄我的老居
它袒露在眼前的窘迫,如
父亲瘦弱的筋骨,母亲干瘪的乳房
可它丑陋的影子,却依旧如
冬日的暖阳
从脚底温到发髻
新房子,长出记忆之花
依然烂漫
离开故园是在第二天的早晨,在村口,我回望我的故里,乡愁顿时又袭上了心头。故乡在变,它会变得更加美好,更加富裕,更加靓丽。可我仍是希望,那些曾经的美好不会消失。也许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已习惯怀旧,多愁善感,也许思想不能与时俱进了,但又分明感觉不到自己错在哪里,那就让曾经的美丽永远留存在记忆的深处吧。
我向雾霭中的故乡深深地鞠了一躬。
(朱卫军,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临沂市文学院副院长。著有散文集《故土的馈赠》、《乡城》、《夜潮地》、诗集《故土的情韵》、长篇报告文学《辉瑞梦 兰陵情》(合著),另有部分中短篇小说散见于报刊,部分作品全国、省、市文学奖。)
壹点号 朱卫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