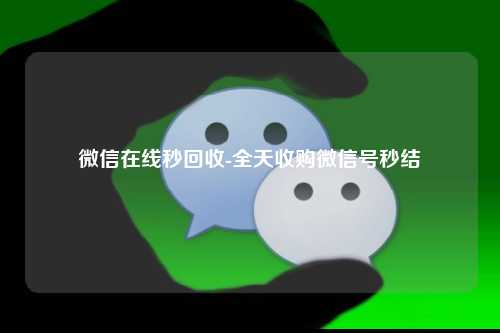师铤
前几日从渭南北站下车,街边遍寻共享单车之际,于花花草草中,看见大片大概是黄花菜的观赏植物——百合花一样的橘黄色花朵,应该就是黄花菜。作为一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之人,对于这个结果,我是不大笃定的。但是,作为一名前中文系学生,黄花菜又叫萱(又写作谖xuan)草、忘忧草,这个我可是知道的。至于为什么把一道菜叫忘忧草,据说从前游子离家,是要在母亲居住的北堂种些萱草,借以减轻思念而忘忧。唐人孟郊就曾经写过“萱草生堂阶,游子行天涯。慈亲倚堂门,不见萱草花。”所以很长一段时间,萱草被赋予母慈子孝之意,萱堂就是母亲居住之地的雅称,和代称父亲的椿庭凑一起,比喻父母都健康的“椿萱并茂”,就是从这儿来的。

傅抱石《云中君和大司命》 此画曾拍出2.3亿元天价,画中描写了屈原《楚辞·九歌》中的两位神话人物———云中君、大司命。
但是目前,说起黄花菜,哦不,萱草,最早的文学记录应该是《诗经·卫风·伯兮》,思念远征丈夫的妻子吟诵出“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痗(mèi)”(哪儿去找忘忧草?把它种到屋北面。一心想着我丈夫,使我伤心病恹恹)。注疏说“北堂幽暗,可以种萱”——从当年文学史课上到现在,我都没搞懂,怎么母慈子孝的忘忧草就和思妇扯一起了?
话扯远了,自此以后,在中国文人的笔下,萱草就不断出现。汉时李陵说:“亲人随风散,沥滴如流星。愿得萱草枝,以解饥渴情”。嵇康《养生论》里说:“合欢解忿,萱草忘忧,愚智所共知也。”南朝谢惠连说:“积愤成疚痗,无萱将如何。”比他晚了几十年的王融说:“思君如萱草,一见乃忘忧。”到了唐,我们渭南乡党白居易也写出了:“杜康能散闷,萱草解忘忧。”
不仅入诗,萱草还入画。除了那些著名的特写外,文征明有一副《携琴访友图》,作此画时,他正辞官在家,学着师傅沈周,一天天就在苏杭之地游山玩水,写字画画。这一幅画里,文征明友人的院前案头,都有萱草的影子。
想起文征明也曾画过很多茶画,无非是携茶访友或者以画换茶的恬淡之作,千百年后,纵然画纸泛黄,那茶香琴韵萱草花,在山中岁月长的悠然中,历久弥新。
当然,在北站口看见那一大堆萱草的时候,我还没有想这么多。我当时只是从《伯兮》想到了《诗经》里虽然有好多花花草草,但是那么多人,从庙堂之上的文官到田间地头的思妇,他们所有人吟诵出的花花草草,大概都没有屈原多。
而一想到屈原同学,我就下意识的,脑壳疼。
当年学文学史,负责先秦文学的是一位老学究,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一名有摄影机记忆的老学究。他的记忆力有多厉害呢?已经退休的人了,还能一字不差的给你背《离骚》《九歌》《天问》,自己背也就算了,还要求我们这些学生背。那段时间,大家见了面,都是一副被屈原害苦了的头疼脸。屈老先生是浪漫主义诗人的鼻祖也就罢了,他还是一名植物学家;植物学家也就罢了,他还是一名精于“报草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他的文章里,除了语气词“兮”,出现频率最高的,就是各种草字头的香草。不信,您看看———“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从文狸,辛夷车兮结桂旗。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路险难兮独后来。”或者“纷总总其离合兮,班陆离其上下。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时暧暧其将罢兮,结幽兰而延伫。世溷溷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这么拗口,读都读不下来,何况背?
当然屈原写文章的时候,可没想过他对后世学子的影响,对他来说,香草恶草,都是抒发情感的手段而已。他以香草自喻,不香的就来比喻奸诈小人。那段时间,疲于背诵的我们,就这样被千年前的失意诗人,搞得天天头疼。以至于快二十年过去了,我看见一大堆艳丽的萱草,高兴了没两分钟,就又头疼了。
虽然害得我们头疼,但是屈原在中国乃至于世界文学史上,都是响当当的人物。他是之后千百年来无数诗人的文学偶像。我的头号男神李白说:“屈平辞赋悬日月”。是啊,没有屈原开创的浪漫华丽的楚辞传统,李白大概写不出《梦游天姥吟留别》《蜀道难》《将进酒》等一大堆名作。李白之外的另一位大诗人,我的二号男神苏东坡也说:“吾文终其身企慕而不能及万一者,惟屈子一人耳!”就是浪漫主义诗人之外的柳宗元,也不会写出对答屈原《天问》的《天对》。
说到这儿,想起之前国家航天局宣布将我国行星探测任务正式命名为“天问”,将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命名为“天问一号”,同时公布了首次火星探测任务标识“揽星九天”。关于“天问”这个篇名的含义,东汉的王逸解释说:“何不言问天?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也。”可见,“天问”其实就是问天的意思。《天问》全篇三百七十四句,提出一百七十二个问题,涉及天地生成、历史兴衰、神仙鬼怪等问题,可以说一部先秦版《十万个为什么》。屈原问天千年后,柳宗元被贬谪到屈原曾经生活过的楚地,对于《天问》做出了自己的回答,写下了著名的《天对》。在柳宗元看来,屈原的很多疑问,都源自当时的神话传说,并不可信。跟屈原比起来,千年后的柳宗元对宇宙的态度显然更接近于今天的科学观。然而,不管是屈原千年之后的柳宗元,还是柳宗元千年后的我们,对“日月安属?列星安陈?”仍然充满了好奇之心。正是怀着这样的好奇之心,今天的科技工作者,要用科学的探索实践,来回答屈原的“天问”。
当然对于没有背诵任务的普通人来说,大家提起屈原,第一反应还是粽子和端午节。事实上,这是一个误会。屈原之前,老祖宗就在吃粽子过端午。这两件事,都不是因他而起的。

张大千《宜男多子图》 在中国画中,萱草与石榴的组合,称为“宜男多子”,萱草与寿石的组合,则称为“宜男多寿”。
曾经,人们认为五月是“恶月”,五月初五即是“恶月恶日”,大概是因为时值仲夏,蚊虫滋生,稍不注意,容易生病。于是“驱瘟避邪”成为这个日子的重点,比方斋戒沐浴插菖蒲喝雄黄酒等。成书于西汉(这会儿离屈原投江不过二三百年)的《礼记·月令》说仲夏之月,“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就是说五月有夏至,阳气达到顶峰,阴气开始回归,阴阳二气争斗激烈,正是万物死生之界。
古人有多忌讳“恶月恶日”?比《礼记·月令》成书还早的《史记》这样写孟尝君:初,田婴有子四十余人。其贱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婴告其母曰:“勿举也。”其母窃举生之。及长,其母因兄弟而见其子文於田婴。田婴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顿首,因曰:“君所以不举五月子者,何故?”婴曰:“五月子者,长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就是当时流传说五月生出来的小孩长到门高的时候就要克父母,所以五月五日出生的孟尝君,差点被封建迷信害死在摇篮。
把客观存在的日期人为地划分为凶恶或者吉利,当然是不科学的。但是在那个科学技术不发达,医疗手段落后的千年前,古人们对于因为气温和湿度上升导致的毒虫肆虐,疾病增多,生活乃至生命被威胁而产生莫名恐慌,从而将希望寄托在神鬼之说,是必然的时代局限性。
话扯远了,这么敏感的日子,老百姓忙着避邪驱灾,统治者也没闲着,毕竟,这个时节是否风调雨顺,关系着一年的农业收成。不过那会儿不是端午祭祀,而是夏至祭祀。据说古时候祭祀夏至,就是用粽子。与之相对应的,是具有“送瘟”意义的龙舟。
自先秦至今,已经两千多年过去了,不管是曾经种于北堂,象征着母慈子孝的忘忧草变成了盘中清香的黄花菜,还是流传千年变化不断的端午夏至,多少习俗,在时光流转中,不断变化。但是不变的,是我们对母慈子孝的珍惜向往,是我们对屈原这样“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的爱国主义诗人的推崇和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