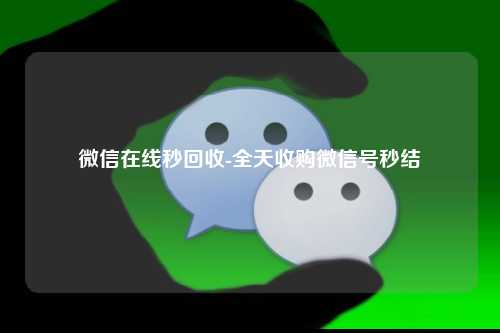藏书印是古代公私藏书的标记。
在众多私人藏书印中,告诫后人的“永宝”印是最多的。例如宋贾似道的“贾似道图书 子孙永宝之”;明代祁承(火業)的“主人手校无朝夕 读之欣然忘饮食 典衣市书恒不给 后人但念阿翁癖 子孙益之守弗失”,张燮的“平生减产为收书 三十年来万卷余 寄语儿孙勤洛诵 莫令弃掷饱蟫鱼”,施大经的“古人以借鬻为不孝 子孙其永宝之”,钱谷的“百计寻书志亦迂 爱护不异隋侯珠 有假不返遭神诛 子孙不宝何其愚”,吕坤的“吕氏书籍 传家读书 子孙共守 不许损失借卖 违者茔祠除名 万历七年坤记”,毛晋的“吾家业儒 辛勤置书 以遗子孙 其志何如 后人不读 将至于鬻 不如禽犊 若归他室 当念斯言 取非其有 无宁舍旃”,清万言的“吾存宁可食吾肉 吾亡宁可发吾椁 子子孙孙永无鬻 熟此直可供饘粥”,张敦仁的“古今珍藏 子孙永保”,王昶的“二万卷 书可贵 一千通 金石备 购且藏 剧劳勚 愿后人 勤讲肄 敷文章 明义理 司典故 兼游艺 时整齐 勿废坠 如不材 敢卖弃 是非人 犬豕类 屏出族 加鞭箠 述庵传诫”,吴兰修的“石华藏书 子孙永宝 鬻及借人 是皆不肖”,沈廷芳的“购此书 甚不易 遗子孙 弗轻弃”,杨以增的“禄易书 千万值 小胥钞 良友治 阁主人 清白吏 读曾经 学何事 愧蠹鱼 未食字 遗子孙 承此志”,王闻远的“我性最喜藏书 所藏数十万 皆从减衣缩食而来 每当披览 拭几焚香 松雪六勿之戒 毕生谨守弗替 子孙得我书者 岁必繙阅 暑必曝晒 慎毋滥借亲朋 慎毋涂鸦损坏 慎勿善贾求沽 世世保之 守而勿坠 真我孝子顺孙也 时康熙丙戌七夕前三日莲泾居士识”,毛扆的“毛氏图书 子孙永宝之”,王献臣的“王氏图书 子子孙孙宝之”,朱钟铉的“子子孙孙永宝用”,徐良士的“子孙宝之”,翁方纲的“子孙保之”,徐谓仁的“子孙保之”,忠彻的“子孙永保”,等等。过去,我们看到此类印章,动辄谴责古人“自私”、“保守”,其实,事出有因:第一,藏书来之不易。他们数十年如一日节衣缩食、省吃俭用,一本一本买来,如清孙儆的“二十年心血所得”沂虞卿的“嘉兴沂虞卿三十年精力所聚”,高士奇的“江村三十年精力所聚”,黄丕烈的“荛圃卅年精力所聚”,缪荃孙的“小珊三十年精力所聚”等印章,都说明藏书之难。万卷藏书,并非一日之功,几十年来,他们露钞雪纂、篝灯呵冻,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他们“食去重肉,衣去重彩,首无明珠翡翠之饰,室无涂金刺绣之具”,每本书都有聚散常的故事,每本书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有的图书甚至是他们一笔一笔钞出来的。例如谢浦泰有“钞书老更痴”,钱谷的“钱谷手钞”,清毛扆的“每爱奇书手自钞”,吴翌凤的“翌凤手钞”,张师亮的“桐山张筱渔氏手钞秘籍”,张宗櫹的“好古楼钞本”,鱼元傅的“每爱奇书手自钞”,郭协寅的“石斋钞书”,黄廷鉴的“每爱奇书手自钞”等印章,都说明了钞书之难。既然藏书来之不易,他们当然希望子孙永宝(保)。第二,前车之履,后车之鉴。历史上重演的许多子孙后代卖书的故事,为藏书家敲响了警钟。
清代罗华在看到藏书家洪颐煊子孙卖光图书时写过一首诗:“十年前记过筠轩,今日犹存竹满园。先后与君同一慨,买书人有卖书孙。”是的,前代买书、后代子孙卖书的故事举不胜举。早在宋代,就有不少子孙卖尽先人藏书的故事,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五云:“藏书之富,如宋宣献、毕文简、王原叔、钱穆父、王仲至家及荆南田氏、历阳沈氏,各有书目。谯君祁氏多书,号外府太清老氏之藏室,后皆散亡,田、沈二家不肖子,尽鬻之。”其中,宋宣献即宋绶,毕文简即毕士安,王原叔即王洙,钱穆父即钱勰,田氏即田伟,沈氏即沈立。另外,宋代藏书家江正、陈亚、姚铉、王钦臣、李光、石公弼、诸葛行仁的藏书也多散佚于子孙之手。江正,字元叔,江南人,宋初著名藏书家,据郑毅夫《江氏书目记》:“正既没,子孙不能守,悉散落于民间。火燔水溺,鼠虫啮弃,并奴仆盗去,市人裂之以藉物。有张氏者,所购最多,其贫乃用以为爨,凡一箧书为一炊饭。江氏书至此穷矣。”陈亚,字亚之,扬州人,藏书数千卷、名画1000余幅。因得双鹤及怪石异花,作诗告诫子孙云:“满屋图书杂典坟,华亭仙客岱云根。他年若不和花卖,便是吾家好子孙。”死后不久,书画等被子孙卖光,便散落民间。王钦臣,字仲至,宋城人,赐进士及第,历仕秘书少监、集贤殿修撰等职,徽宗时,知成德军。藏书43000卷。其孙王问时不能守书,一心仕进,献出“镇库书”,混了个小官,“诏特补承务郎”。姚铉,字宝臣,庐州人。太平兴国八年(983)进士,历仕殿中丞、两浙转运使等职,北宋著名藏书家。死后子孙不能守,其子姚嗣复想当官儿,“以其书上献,授嗣复永城主簿”。石公弼,字国佐,越州新昌人,北宋著名藏书家。死后,其子“颇弗克守,鬻于从子石邦哲而尽”。李光,字泰发,越州上虞人。藏书数万卷,死后,“子孙不肖,粗率鄙俗,不能保守,而为乡里豪民所得”。诸葛行仁,会稽人,著名藏书家,绍兴五年(1135)六月,诏求遗书,献书8456卷,诏官一子。沈立,字立之,历阳人。天圣八年(1030)进士,历仕两浙转运使、谏议大夫等职。藏书3万卷,有《沈谏议书目》三卷,死后,子孙尽鬻之。田伟,原籍北京人,后占籍江陵,藏书37000卷,有《田氏书目》六卷。政和中,诏求遗书,其子献书千卷,诏官其子。元代藏书家子孙卖掉藏书者有贺铸、虞堪、袁桷、庄肃等。贺铸,字方回,卫州人。藏书万余卷,藏书处为企鸿轩。其书在南宋时,已为子孙鬻于市。后来,次子贺廪又献贺铸校书5000余卷,诏官平江府粮料院。虞堪,字胜伯,长洲人。著名藏书家,藏书处为城南佳趣。其书递经虞镛、虞湜、虞权收藏,至虞权时,家贫,“尽斥卖先世故物,以供衣食。权死时,胜伯所藏词翰,无虑数箧,妻子以鱼罾裹置屋梁。久之,并其罾亡矣,吴中故世儒家,虞氏与南园俞氏为最。两家入明朝,至永乐中而微,至弘治初而绝。征文献者,为三叹焉”。袁桷,字柏长,鄞县人。元代著名文学家和藏书家,有《廷祐四明志》、《清容居士集》等著作。死后,子孙不能守,或被子孙转卖,或被奴仆毁坏,逐渐散佚。庄肃,字恭叔,号蓼塘,松江人。藏书八万卷,经史子集,无所不有,元文宗时,在一次经筵活动时,文宗“语及唐聂夷中诗,询问其有文集否”,诸学士以未闻对。或言庄氏富藏书,特旨访其家,果有聂集,上之,欶封教授。元顺帝时,编撰宋辽金三史,诏求遗书,危素专程来到庄家买了500卷而去。又据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七:“蓼塘既没,子孙不知保惜,或为虫鼠蚀啮,或为邻盗窃,或供饮博之需,或应(饣胡)覆之用,编怢散乱,所存无几。”
焦竑、陈第、谢肇淛、徐(火勃),曹学佺,马思赞、毛晋等明代藏书家其藏书均散佚于子孙之手。焦竑,字弱侯,原籍日照,后迁南京。明代著名藏书家,有《焦氏藏书》二卷,藏书处为澹园抱瓮轩、竹浪轩等。据黄宗羲《天一阁藏书记》:“余在南中,闻焦氏书欲卖,急往讯之。不受奇零之值,二千金方得为售主。时冯邺仙官南纳言,余以为书归邺仙,犹归我也,邺仙大喜。及余归而不果,后来闻亦散去。”也就是说,焦竑藏书初欲售黄宗羲而未果,最后还是散佚了。陈第,字季立,连江人,明代将军藏书家,藏书处为世善堂、倦游庐等。其《世善堂书目》自序云:“自少至老,足迹遍天下。遇书辄买,若惟恐失,故不择善本,亦不争价值。又在金陵焦太史、宣州沈刺史家,得未曾见书,钞而读之。积三四十余年,遂至万有余卷。纵未敢云汗牛充栋,然以资见闻,备采择,足矣足矣。”鲍以文《世善堂书目》跋云:“明万历间,连江陈第手自编定,子孙时时增益。藏弆二百余年,后嗣不复能守。乾隆初年,予按其目求之,积四十年,一无所得。则当时散落,诚可惜也。”又据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余游闽,林秀才侗持第后人所辑《世善堂书目》求售。灯下阅之,见唐五代遗书琳琅满目,如披灵威、唐述之藏,多平生所未见,不觉狂喜。秀才许至连江代购,逾年得报,书则已散佚,徒有惋惜而已。”也就是说,陈第的藏书延续了200多年,终因“后嗣不复能守”而散佚。谢肇淛,字在杭,长乐人。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历仕湖北推官、南京刑部主事、兵部郎中、广西按察使等职。著名藏书家,藏书处为小草斋。死后子孙不能守,散佚殆尽。虞守愚,字惟明,义乌人。嘉靖二年(1523)进士,历仕嘉鱼知县、大理寺左丞、刑部尚书等职。著名藏书家,藏书处为东崖书舍。死后,子孙不能守,廉价售于胡应麟,据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三:“胡元瑞书,盖得之金华虞参政家者。虞藏书数万卷,贮之一楼,在池中央,小木为杓,夜则去之,榜其门曰:‘楼不延客,书不借人’。其后子孙不能守,元瑞啖以重价,绐令尽室载至,凡数巨艦,及至,则曰:‘吾贫不能偿也。’复令载归。虞氏子既失所望,又急于得金,反托亲识居间,减价售之,计所得不十之一也,元瑞遂以书雄海内。然书目竟未出而元瑞下世矣,恐其后又蹈虞氏之辙也”。可见胡应麟(字元瑞)巧取虞书,遂雄海内。王元美先生为作《酉室山房记》,然而,正如谢肇淛所预言,胡应麟自己“又蹈虞氏之辙也”,下面就介绍一下胡应麟。胡应麟,兰溪人。藏书42384卷,藏书处为少室山房、二酉山房。死后,三子尚幼,家境渐趋败落。不久,藏书散佚殆尽,连同房屋一起卖给同乡进士唐骧,易名古梿书屋,章有成曾经来过这里,今昔对比,惨然赋诗云:“空余池馆胜,遥想旧登临。当代词章手,穷年著作心。六书翻乌迹,四部陋蝉吟。寂寞玄亭下,桓谭独赏音。”马思赞,字寒中,海宁人。著名藏书家,藏书处为道古楼、红药山房等。死后,“其子好樗蒲,已准百钱落博徒之手矣。”也就是说,马思赞的藏书散于博徒之子手中。毛晋,字子晋,常熟人,明末清初的著名藏书家和出版家。藏书84000册,藏书处为汲古阁等,毛晋死后,起初五子毛扆尚能继承父业,继续藏书和刻书。但是不久,毛家产业渐趋衰败,入不敷出,善本逐渐售出。宋元善本先是卖给泰州季振宜,后来季氏又转卖给徐乾学传是楼。《十三经注疏》和《十七史》卖给席氏扫叶山房;《十元人集》卖给无锡华氏。毛扆还编了一本《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这是一部包括477部善本的售书广告,每书包括书名、版本、售价和小注。标志着毛氏藏书已经到了穷途末路。其实,明代藏书家的藏书散佚于后世的例还有很多。据郑杰《红雨楼题跋》序:“吾闽藏书之富,嘉靖后历历可数,陈方伯暹、马恭敏森、林方伯懋和、王太史应钟。乃马公季子能读,陈公后昆寝微,散如云烟;王、林二公捐馆未几,书尽亡失,飘荡四方。”清代藏书家张昭、朱彝尊、吴焯、全祖望、鲍廷博、周锡瓒、陈鳣、刘桐、袁廷梼、李诚、徐松、王懿荣、李嘉绩、沈曾植、徐绍棨、路慎庄、陆懋勋、凌霞等的藏书亦散佚于子孙之手。张昭,字力臣,山阳人。藏书家,藏书处为符山堂。曾捐资为顾炎武刻《广韵》、《音学》等五书,顾炎武云:“笃信好古,专精六书,吾不如张力臣。”死后,子孙不能守,将五书版卖给李光地,得五百金。朱彝尊,字锡鬯,藏书八万卷,藏书处为曝书亭。其孙朱稻孙“贫不能宁,即渐归散佚。阮元于嘉庆中,按试嘉兴,即言‘曝书亭久废为荒田,南北垞种桑皆满,亭址无片甃’。”吴焯,字尺凫,钱塘人。著名藏书家、出版家,藏书处为瓶花斋。嘉庆五年(1800),子孙不能守,将瓶花斋旧藏卖给陶士秀,得银24两,其中颇多佳本。全祖望,字绍衣,鄞县人。乾隆进士,藏书家,藏书处为鲒绮亭。后世子孙“以遗书为故纸,权其斤两而卖之,虽先集亦与焉,遂荡然无一存者”。鲍廷博,字以文,原籍歙县人,移籍杭州。著名藏书家和出版家,藏书处为知不足斋。死后,子孙不能守,多所斥卖。道光、咸丰间,钞校诸本分别卖给仁和劳氏、归安陆氏、杭州丁氏等。周锡瓒,字仲涟,号香岩,长洲人。著名藏书家,藏书处为水月亭、香岩书屋等,死后,子孙不能守,黄丕烈《学斋占毕》跋云:“香岩作古,书多分散,儿孙有不爱此,或并借此先世宝藏声名,挟册索重值获利,故肯赠人。予亦重是故友物,必勉力购之。此时聊厌我欲,聊尽我情耳,安知我之儿孙不犹是耶?”可见黄丕烈虽然买到周书,但也担心自己的子孙也会把藏书卖光。陈鳣,字仲鱼,海宁人,著名藏书家,藏书处为津逮舫、向山阁等。死后,其藏书多为子孙卖掉。吴衡照《海昌诗叙》云:“殁不数载,后人无识,为苕上书贾赚去,题识宛然,图记犹昔,精钞旧刻,以其族行,吁可伤矣。”刘桐,字秋崖,乌程人。藏书家,藏书处为眠琴山馆,死后,其藏书多为子孙卖掉,张鉴《眠琴山馆藏书目》序云:刘桐“一病遽归道山,其家不能收拾。子幼,为人荧惑,举十余万卷之书,一旦畀之他人。飘风好鸟,变幻若此,斯可叹矣。”范锴《毕笑庼杂笔》卷六云:“(刘桐)子幼,山馆之书无人司理,竟为族戚鼠窃鲸吞,竞博书贾之利,不数月悉归乌有。其罹厄之速,又古所未闻,为之三叹。”袁廷梼,字寿阶,吴县人。藏书七万卷,藏书处为五砚楼等。死后,藏书多为子孙卖掉,其婿贝墉《履斋示儿编》序云:“先外舅去秋骤病溘化,手聚数万卷,一旦乌有,五砚楼头乃有赵清常武康山中之哭,回首夙昔,墉也何心而握管?”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周此山诗集》云:“漫说收藏五研楼,人亡人得已堪忧。而今楼在人何在,手触遗编涕泗流。”李诚,字师林,黄岩人。藏书家,藏书处为敦说楼。死后,子孙不能守,斥卖他人,“每本仅钱十文,购者稍多,增至三十文。反嫌稿本字迹模糊,覆瓿糊壁,付火者所在多有”。徐松,字星伯,原籍上虞人,移籍顺天,藏书万卷,藏书处为荫绿轩等。死后,子孙不能守,大半斥卖,散佚殆尽。王懿荣,字正孺,福山人。著名藏书家,藏书处为天壤阁、天绘阁等。死后,子孙不能守,所藏图书、金石散佚。后人曾将图书抵押于书估,积久益贫,不能复取。欲售之押主,屡磋书值,仅得四千元。李嘉绩,字云生,通州人。藏书52000卷,藏书处为五万卷阁、代耕堂、双桐书屋等。死后,子孙不能守,家无余财,柯逢时以数万金购所得书而去”。柯逢时致函缪荃孙云:“李云生大令书昨经陕友运来,已为购得。无甚秘本,惟西北藏书,此间亦有无可搜罗者”。沈曾植,字子培,嘉兴人。光绪六年(1880)进士,历仕江西广信知府、安徽布政使等职,藏书家,藏书处为海日楼、全拙庵、潜究室等。死后,子孙不能守,其藏书“由其嗣子慈护以二十万金让与陈人鹤”。徐绍棨,字信符,原籍钱塘,移籍番禺。藏书数万卷,藏书处为南州书楼。死后,子孙不能守,“其女曾选出善本一批装十箱,存澳门,现除广东文献外均售于富商姚某,得葡币四万元。南州书楼有词曲八百种,稍前仅以八百余元转让于人”。路慎庄,字子端,盩厔人。道光十六年(1836)进士,历仕翰林院编修、给事中等职。藏书68600卷,藏书处为蒲编堂。死后,子孙不能守,尽行斥卖。叶昌炽云:“其后人筮仕于准,乙酉(光绪十一年)之秋,梱载遗书到吴求售。余曾得旧刻数种。有正统本两《汉书》,陈简庄叹为至佳者,为丁泳之丈所得,至今犹悬梦寐中也”。陆懋勋,字勉侪,仁和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进士,历仕翰林院编修等职,藏书家。死后子孙不能守,“存书七十箱,为童騃所弃。每箱二元,售与抱经堂书肆,至可伤也。《杭州府志稿》三十二册为杨氏丰华堂所收”。凌霞,字子与,归安人。藏书家,藏书处为癖好堂。死后,子孙不能守,“书贾挟其藏书至沪,大半归之芝阁庞氏。庞病殁,遂分售南北,流转四方”。古代藏书史上,藏不数代、代不数人之例实在太多。当然,也有世代相传的例子。王铚,字性之,汝阴人。王莘之子,藏书数万卷,南宋著名藏书家。死后,长子王廉清能守其书。据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二:“(王铚)既卒,秦嬉方恃其父气焰熏灼,手书移郡,将欲取其所藏书,且许以官其子。长子仲信,名廉清,苦学有守,号泣拒之曰:‘愿守此书以死,不愿官也。’郡将以祸福诱胁之,皆不听。熺亦不能夺而止。”秦熺之父秦桧为南宋权臣,一手遮天。王廉清能够顶住各种诱惑,坚不同意,实属不易。但是,这在古代是很少见的,很多藏书家的后人大多经不住名利的诱惑,当了名利的俘虏。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古代藏书家鉴于历史教训,为了严防藏书散佚,采取了不少措施:(一)转赠他人,即把藏书转赠给可以依赖的人,以便死后藏书永久流传。宋代井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井度,字宪孟,南阳人。历仕四川转运使、郢州防御使等职。酷爱藏书,藏书数万卷,死前把藏书全部移赠给晁公武,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序说:“(井度)素与公武厚,一日贻书曰:‘某老且死,有平生所藏书,甚秘惜之,顾子孙稚弱,不自树立,若其心爱名,则为贵者所夺;若其心好利,则为富者所售,恐不能保也。今举以付子,他日其间有好学者归焉。不然,则予自取之。’公武惕然从其命,书凡五十箧,合吾家旧藏,除其复重,得二万四千五百卷有奇。今三荣僻左少事,日夕躬以朱黄雠校舛误,每终篇辄撮其大旨论之,岂敢效二三子之博闻,所期者不坠家声而已。书则固自若也,傥遇其子孙之贤者,当如约。”明代藏书家杨循吉也是一个例子。杨循吉,字君谦,吴县人,成化二十年(1484)进士,历仕礼部主事等职。有《攒眉集》、《奚囊百镜》、《松筹堂集》、《南峰乐府》等著作。藏书10万余卷,藏书处为雁荡村舍。鉴于子孙多不能守的惨痛教训,死前他把藏书赠送给亲戚朋友,《人海记》云:“杨循吉既老,散书与亲故云:‘令荡子爨妇无复著手。’亦一道也。”杨循吉《题书厨诗》云:“吾家本市人,南濠居百年。自我始为士,家无一筒编。辛勤二十载,购求心颇专。小者虽未备,大者亦略全。经史及子集,一一义贯穿。当怒读则喜,当病读则痊。恃此用为命,纵横堆满前。当时作书者,非圣亦大贤。岂待开卷看,抚弄亦欣然。奈何家人愚,心惟财货先。坠地不肯拾,断烂无与怜。朋友有读者,悉当相奉捐。胜付不肖子,持去将鬻钱。”死前把藏书转赠他人,釜底抽薪,就从根本上解决了藏书散佚的问题。(二)标识书价。为了防止后人贱卖藏书,藏书家死前已审定价格,明代项元汴、清代毛扆就是这样。项元汴,字子京,号墨林,秀水人。著名藏书家,藏书处为天籁阁。其藏书朱印累累,多标书价。沈炳巽《权斋老人笔记》云:“禾中项墨林每书后必记所得之价以示后人,使不贱售。”其藏宋版《周易》卷尾有题识云:“万历辛丑,得于毕亭何氏,用价一百二十金。”宋版《北山录》卷尾题“原值壹金。”对于项氏这种不惜高价购求图书而胡乱钤印、题字的做法,后人多所非议,清姜绍书《韵石斋笔谈》云:“墨林生嘉靖、隆庆之世,资力雄赡。享素封之乐,出其余绪,购求法书名画,及鼎彝奇器,三吴珍秘,归之如流。每得名迹,以印钤之,累累满幅。亦是书画之一厄。譬如石卫尉以精珠明镠聘得丽人,而虞其他适,则黥面而记之。抑且遍黥其体,使无完肤,较蒙不洁之西子,更为酷烈矣。复载其价于楮尾,以示后人。此与贾竖甲乙账簿何异。不过欲子孙长守,纵或求售,亦照原值而请益焉,贻谋亦既周矣。”尽管如此,项氏藏书并没有世代流传,早已荡然无存,朱彝尊《还乡口号》诗云:“墨林遣宅道南存,词客留题尚在门。天籁图书今已尽,紫茄自苋种诸孙。”毛晋第五子毛扆,开始还能继承父业,继续藏书和刻书。没有多久,家业衰败,入不敷出,开始变卖毛氏藏书,后来干脆用广告的形式编了一个《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标明书名,版本、银两,公开出售藏书。这样,鼎鼎大名的毛晋汲古阁从此销声匿迹。(三)刻书,即把善本书雕版印刷,大量复制,这是藏书家严防藏书失传的重要途径。当然,其中题跋、刻书不乏功利等思想,但是不可否认,传播古籍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五代的毋昭裔。据记载:“毋公者,蒲津人也,仕蜀为相。先是公在布衣日,尝从人借《文选》及《初学记》,人多难色,公浩叹曰:‘余恨家贫,不能力致。他日稍达,愿刻板印之,庶及天下习学之者。’后公果于蜀显达,乃曰:‘今日可以酬宿愿矣。’因命工匠日夜雕板,印成二部之书。公览之,欣然曰:‘适我愿兮。’复雕九经诸书。”清代藏书家鲍廷博在藏书跋语中说:“历数近来藏书家,而自述其储蓄之富。曾几何时,悉已散为烟云。渺兹一粟,漂流沧海中,杳不知其所之矣。因概死生旦暮,聚散无常。予家所藏,异时岂能独保,徒令后人复哀后人耳。间尝语儿辈,与其私千万卷于已,或子孙不为之守,孰若公一二册于人,与奕禩共永其传。此区区校刻丛书之苦心,窃欲共白于当世,而一为之劝也。”这是清嘉庆十年鲍廷博(1805)七十八岁时在其所刻元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后所写的一段跋语。可见其刻书之目的在于传播书籍。历代私人藏书家刻书者多如牛毛,宋代如朱熹、周必大、陆游、廖莹中等;元代姚枢、顾瑛、岳浚、李漳、刘贞等;明代朱承爵、许宗鲁、洪楩、袁褧、顾元庆、顾起经、郭云鹏、闻人铨、范钦、范惟一、王世贞、张佳胤、吴勉学、吴琯、冯梦祯、张燮、李之藻、曹学佺、臧懋循、徐(火勃)、胡正言、毛晋等;清代周亮工、朱彝尊、徐乾学、卢文弨、袁枚、鲍廷博、吴骞、孙星衍、张海鹏、黄丕烈、阮元、梁章钜、秦恩复、金山钱氏、伍崇矅、汪士钟、缪荃孙、王先谦、叶德辉、罗振玉等。这些藏书家刻印了许多世不多见的善本书,为古籍的流传作出了重要贡献。(四)借阅,即敞开藏书,一改古人秘不示人之风,任人借阅。这也是严防图书失传的重要途径。这种开放型藏书家,虽然人数不多,但是一反时代潮流,非常可贵。这类印章又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曾在×××”、“曾藏×××”。如清代丁丙的“曾藏八千卷楼”、刘惺棠的“曾在东山刘惺棠处”、何广熹的“古闽何氏丁戌山馆曾藏”、何瑗玉的“曾藏何蘧庵处”、李馥的“曾在李鹿山处”、沈慈的“曾在云间啸园沈氏”、张金吾的“曾在张月霄处”、陆僎的“曾在陆树兰处”、陆艺荣的“曾在萧山陆氏香圃处”、林鸿年的“曾在林勿村处”、郁松年的“曾在上海郁泰峰家”、赵元方的“曾在赵元方家”、钱天树的“曾藏钱梦庐家”、蒋琦的“蒋绚臣曾经秘藏”、鲍廷博的“曾在鲍以文处”。藏书家把藏书的流传看作一个过程,自己仅仅是其中一个暂时收藏者,并没有把私人藏书看作个人的固定资产;任人借阅。二是有“××读过”、“××曾观”等字样。例如清永瑢的“永瑢曾观”、朱学勤的“修伯读过”、朱昆田的“朱西畯曾观”等印表示,藏书家作为一个读者,曾经读过这本书,相当于阅览室的“读者登记簿”,至于今后谁再来读,都可以,反正我是其中一个读者。三是有“阅者”、“得者”、“读者”等字样,似在告诉后来的读者和藏书者要珍惜图书、爱护图书。说明图书处在流传过程中,“阅者”、“得者”、“读者”都是暂时的。例如清孙从添的“得者宝之”、许增的“得之不易失之易,物无尽藏亦此理。但愿得者如我辈,即非我有亦可喜。”何元锡的“阅者珍之”,崇恩的“吾钤所藏初即精本,得者宝之,庶垂久远”,彭元瑞的“遇读者善”。四是直接标明“借观”、“借读”等字样,说明藏书可以借阅。例如清卢文弨的“文弨借观”和“文弨借阅,精校善本,得者珍之”,钱天树的“梦庐借观”,叶名沣的“润臣借读”。五是直接标明可以流传的图书,例如清代吴诚、吴焯、吴玉墀等都有一方藏书印:“愿流传 勿污损”。表示对后来人的殷切希望。总之,这五种藏书印都是开放型的。藏书家破除了自私、保守的传统观念,公开藏书,面向社会,是一种极大的进步。(五)遗训,即用藏书印的形式留下遗言,嘱托“子孙永宝(保)”,上文已经多有举例。对于这种藏书印,我们不应该多所指责,不应采取完全否认的态度,应当加以理解。明代杨士奇《文籍志序》云:“夫人于其所好,劳心苦力以求得之,必将谨护珍袭,不至于废坏。逮得传其后之人,未尝知得之之难,盖有视之漠然不以留意,弃之为弃瓦砾者矣。吾惧后之人不知守也,凡书其志吾之所以得,而勉其所以守。盖昔人爱一草一木犹戒子孙以勿坏,矧书籍圣贤至训之所寓乎?”这段话说明了藏书家叮咛“子孙永宝(保)”的原因,其来有自,“而勉其所以守”。